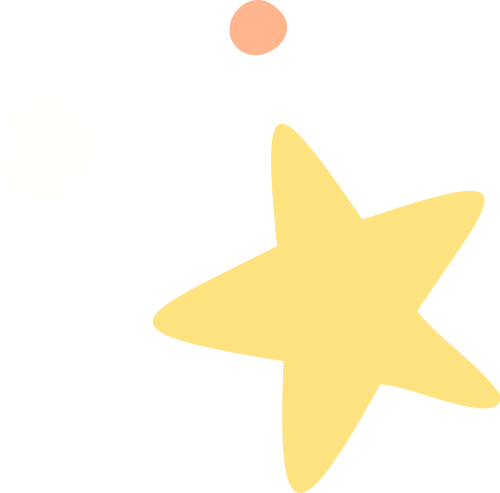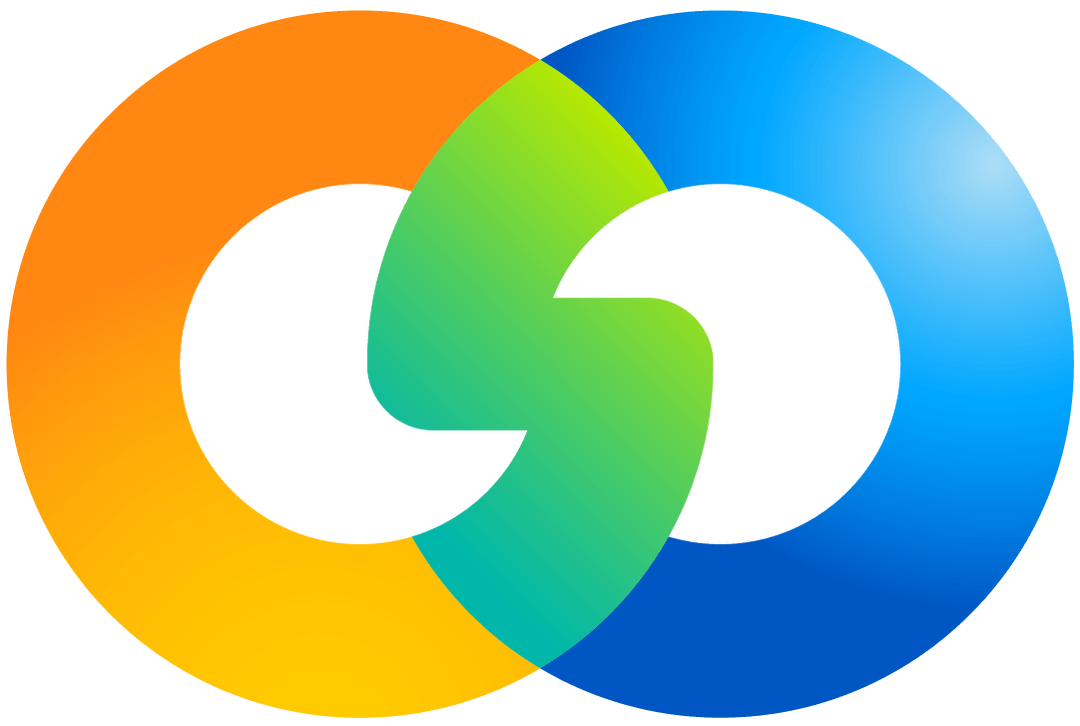
凌晨五点半,矿区的路灯还亮着,柴里煤矿绿化环卫队职工杨丕喜拖着金属义肢,在叮当声里,利索地拿起扫帚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在扫帚划过柏油路面的沙沙声中,偶尔混着假肢弹簧的轻鸣。

“这腿跟了我22年,比铁锹还趁手。”他弯腰拾起落叶,工作服上反光条在路灯下泛着经年的旧光。8100个清晨,巡扫路线早刻进金属关节的每一次屈伸。
草屑里的独舞者
“轰——”打草机的轰鸣,惊飞了梧桐树上的麻雀。杨丕喜斜背着40多斤重的机器,在工业广场东北角游走。草屑裹着尘土在晨光中翻飞,把他瘦高的身影搅成模糊的剪影。
“杨师傅,歇会儿吧!”喊到第三声,他才关掉机器。转身时,护目镜上积了层草灰,工装裤膝盖处磨得有些泛白,假肢连接处的裤子浆洗得笔挺。
“哎,这片杂草倔得很,根扎得深……”他摘下口罩,黝黑的脸上汗珠顺着皱纹沟壑淌下来,在晨光里亮晶晶的。
笔者想搭把手,刚拎起打草机就踉跄了一下。

“这玩意儿得用腰劲。刚用那会儿,端10分钟胳膊就哆嗦了。现在嘛……”他笑着示范,套假肢的右腿蹬住地面,左膝微屈,整个人像张拉满的弓。
“你看,草根要斜着切……”话音未落,只见他单手拎起机器,在空中划了道弧线,一丛茅草已在刀片下簌簌倒地。
工友老王凑过来说道:“别人一天打2箱油,老杨得打3箱。他连墙根儿都不放过。”
环卫队的巧手匠
2002年的春天,永远凝固在杨丕喜的记忆里。一天在回家途中,他意外遇到油罐车爆炸事故,被崩出的铁片炸伤,致右大腿30厘米以下全部截肢。
在病床上睁开眼时,他的妻子正攥着他空荡荡的裤管掉眼泪。



“当时觉得天都塌了,直到看见病房窗台上的绿萝……蔫了半个月的枝条,突然抽出了新芽。”杨丕喜哽咽着说。
2008年,杨丕喜转岗到矿环卫队工作,老队长递给杨丕喜一把竹扫帚问:“要不你在库房管工具?”他摇头,径直走向角落里的绿篱机。
这个倔强的汉子,硬是练出了独腿修剪的绝活:左腿扎马步稳住重心,右腿的假肢当支点,修剪刀在空中划过,带来清新的草味。
“别看杨师傅装了假肢,干起活来那股子韧劲儿,可一点不比别人差。”同事小张倚着修剪机比划道。
“有次我们修剪法桐,树胶把绿篱机的刀口糊得严严实实,没法再使用,只能人工修剪。”小张忽然压低声音,手指在膝盖处画了个圈,“杨师傅二话不说,就把假肢卸下来垫在树根上——金属关节卡着蹲不下去啊!他就这么半跪着捣鼓了整整两小时。”

小张指了指休息室墙角的工具箱,里面静静躺着一把缠满绝缘胶布的老虎钳,斑驳的钳柄末端焊着一截水管。“那是老杨用报废铁管做的‘第三条腿’。”小张笑着轻拍工具柜,“是他平时修剪高处枝桠时支撑身子的,用起来比脚手架还稳当。”
除了这些工作需要的技能,杨丕喜还利用休息时间自学了机械设备维修技术。队里的机器出了故障,他总能“手到病除”。
“也没什么特别的,熟能生巧嘛!”杨丕喜总结道。
矿山新绿的拓荒人
每天临下班,杨丕喜都会巡查一遍矿区新栽的树林。他走得忽快忽慢,深一脚浅一脚的足迹,在松软的新土上格外清晰。“这片广场的地,我们筛了三遍土。”他弯腰扒开土层,露出蚯蚓拱过的痕迹,“你看,活土养出来了。”

突然,他驻足看向远方。顺着他的视线望去,晚霞正给矿山镀上金边,新栽的树苗在春风里舒展枝条。他轻轻抚过樱花树干,掌心的老茧蹭得树皮沙沙响,“马上就会见到花海了。”他说这话时,眼中闪烁着光芒。
当笔者问他为什么每天负重行走不知疲惫,他低头调试着绿篱机的火花塞:“矿工下井要踩稳每一步,我现在每天也在走自己的巷道,这么走着走着,就把春天走出来了。”

夜幕降临,杨丕喜背着工具包往工具房走去,身影渐渐没入渐浓的夜色。他的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,时而与梧桐树影重叠,时而与含苞的樱花交织。